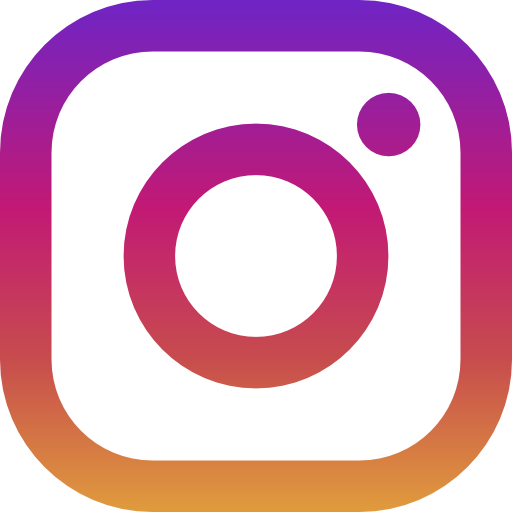作為一個進深的影像活動研究者,張子木回顧剛完滿結束的羅海德首個個展(「文字機器創作集」第六輯),探出有別於一般影像創作的理路、胸襟。Zhang Zimu, advanced researcher of moving image events, sheds light on Hector Rodriguez’s unusual rationale, impulses,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moving-image making as critique, as were articulated in the first solo show he just completed for the the 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 6th edition.
一個女人的面孔在屏幕中來回猶疑。三個屏幕,三種猶疑的運動方式,參數可變,困頓無盡。

這是走進數碼藝術家和理論家羅海德(Héctor Rodríguez)個展時觀者所看到的第一個作品。迷影者不難認出畫面源自英格瑪.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的《假面》(Persona, 1966) 中的一幕:女演員在舞台上突然與角色剝離,驚詫無語。原本短短幾秒,卻被藝術家無限延展。「當一個人突然意識到其表演性且無法再繼續的這個瞬間…,我喜歡。」藝術家如此解釋道。看似輕盈遊戲,卻開啟了一個切中時弊的難題:甚麼是線性電影之外的動態影像?在技術新異的當下,如何理解注入動態影像的技術並且以此創造一種詩性語言?
整個展覽都是圍繞上述這些問題而發出的探尋路徑,藝術家卻並不執着和急於給出答案。如展覽名字「歧路結節,開合解密」所意味的,展場中這些分岔的歧路,閃現着靈感、幽默感與各式複雜的數學公式的相遇。比如作品【Inflections】(拐點)中以非線性方程式產生混沌現象的數學程式(Logistic Map / 物流圖,又譯作「單峰映象」)為依託,將時間影像破壞性地注入運動影像;作品【Fluxions】(流數)從影像壓縮技術中得到靈感而去追蹤一個低成本恐怖片的像素向量運動;或是作品【Approximation Theory】用中文大寫數字作為圖像庫重塑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的經典奧林匹克運動員鏡頭 (Triumph of the Will, 1935) 的平面質感,演繹數學中的「逼近理論」等等。還有一些作品因為算法太過複雜,連藝術家羅海德自己也戲稱「不是給人看的」。可他的創作出發點並不艱深。不像大多藝術家般秉信從藝術理念出發,他的創作總是從一個技術業餘者遭遇到的技術問題開始,問出一個個「傻」問題,待他的合作夥伴數學家 Felipe Cucker 為他解難,若理出來的問題和他嘗試的解決方案不夠清晰、不夠合理,二人便會再埋首一起解決。
回憶當初意慾翻新活動影像的動機,他談到一次在電影院裡看安哲羅普洛斯 (Theodoros Angelopoulos) 的《永遠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 1998),電影中一步一步的鏡頭運動和剪輯安排竟都在他預料之中。他不禁自問,應該怎樣延續對電影的熱愛呢?作為深愛電影以及深諳電影史的藝術家,他延續對影像之愛的方式,是拆解與重組經典電影片段以及面向他個人的觀影趣味和品鑒不滿之作,這個電影清單裡面包含了希區柯克的《第十七號》(Alfred Hitchcock 1932: Number Seventeen),尚盧高達的《阿爾法城》(Jean Luc Godard 1965: Alphaville),貝拉塔爾的《來自倫敦的男人》(Béla Tarr 2007: The Man from London),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等等。在部分作品中,對既有影像片段的再生成還包括整個技術系統的裝置呈現,如作品《Z》中,許多不同灰度的小圓盤橫縱排列,每一幀原始影像的變化都會激發圓盤的旋轉運動和亮度變化,而這種變化並不與傳統意義上的電影技術指標一一對應,而是引用由荷蘭物理學家Frits Zernike 提出的,用作表達光學設備 (optical devices,如顯微鏡)的「畸變」狀態 (aberrations) 的圓形結構出發,繼而生成序列,是一種視覺畫面的整體音樂性泛音(visual overtone)。
 整個展覽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Flowpoints】,數字印刷畫面凝聚的一瞬是應用運動捕捉技術在所選取的畫面幀之間形成的運算渲染線條,不同顏色的軌跡代表軟件運算順序的先後,整體的畫面形象十分抽象但仍可辨認齣電影人物的輪廓以及動態趨勢,一種辯證性的動靜,另類的敘事性 (narrativity),以及璀璨中的「苦力」。是的,羅海德強調,他想讓數字軟件的「隱形」的計算勞動被看到。當然,再一次,這種勞動有時也是藝術家和計算機開的一個玩笑,比如於前後接連的兩幀畫面之間無端的插進沒有內容的黑格,干擾軟件對動勢走向的偵察,標示運算的線條便在延長了的「抓迷藏」過程中頻繁起來,「這時候軟件就瘋了,哈哈!」羅海德咯咯的笑,灰白色短髮也搖動起來。
整個展覽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Flowpoints】,數字印刷畫面凝聚的一瞬是應用運動捕捉技術在所選取的畫面幀之間形成的運算渲染線條,不同顏色的軌跡代表軟件運算順序的先後,整體的畫面形象十分抽象但仍可辨認齣電影人物的輪廓以及動態趨勢,一種辯證性的動靜,另類的敘事性 (narrativity),以及璀璨中的「苦力」。是的,羅海德強調,他想讓數字軟件的「隱形」的計算勞動被看到。當然,再一次,這種勞動有時也是藝術家和計算機開的一個玩笑,比如於前後接連的兩幀畫面之間無端的插進沒有內容的黑格,干擾軟件對動勢走向的偵察,標示運算的線條便在延長了的「抓迷藏」過程中頻繁起來,「這時候軟件就瘋了,哈哈!」羅海德咯咯的笑,灰白色短髮也搖動起來。
展廳最中間的一個區域被命名為「閱讀室」(Reading Room),擺放着桌椅,長桌上隨意堆放著跨越哲學、數學、社會學、批評理論、電影研究等學科的著述和筆記,橫跨藝術家研究、教學的二十年。當觀者伸手擺弄、閱讀這些作品思考背後的物質性材料,試圖自行建立一些作品的因果邏輯之時,或許會更加意識到,這些形形式式的影像實驗並不是偶然性或趣味與天賦使然;理論與實踐,技術與人文,在羅海德看來,從來都是緊密關聯,難分彼此。他與策展團隊和這一系列展覽背後的藝術群體「文字機器創作集」(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 所踐行的,是面向人與技術區隔時代的二者的再度聯結。技術,應被看做我們世界中建構性的語言,這也是是次展覽的政治性所在。
(羅海德的作品詳情可參照他的藝術家個人網站 http://concept-script.com)
作者:張子木:香港城市大學博士候選人,動態影像實踐者與研究者
(2018年10月19日)
***推薦閱讀 Recommended reading:
「文字機器創作集」第六輯展覽系列 […] 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 6th edition exhibition series […], 2018.08.31 – 11.18